(共产主义杂志)回顾越南革命史,国家的融入与发展始终与时代的变迁紧密相连。早在建国之初,胡志明主席就在写给联合国的信中明确阐述了越南愿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的精神,表达了“在各个领域实行开放合作政策”的愿望。这可以说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现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待国际社会的第一个“宣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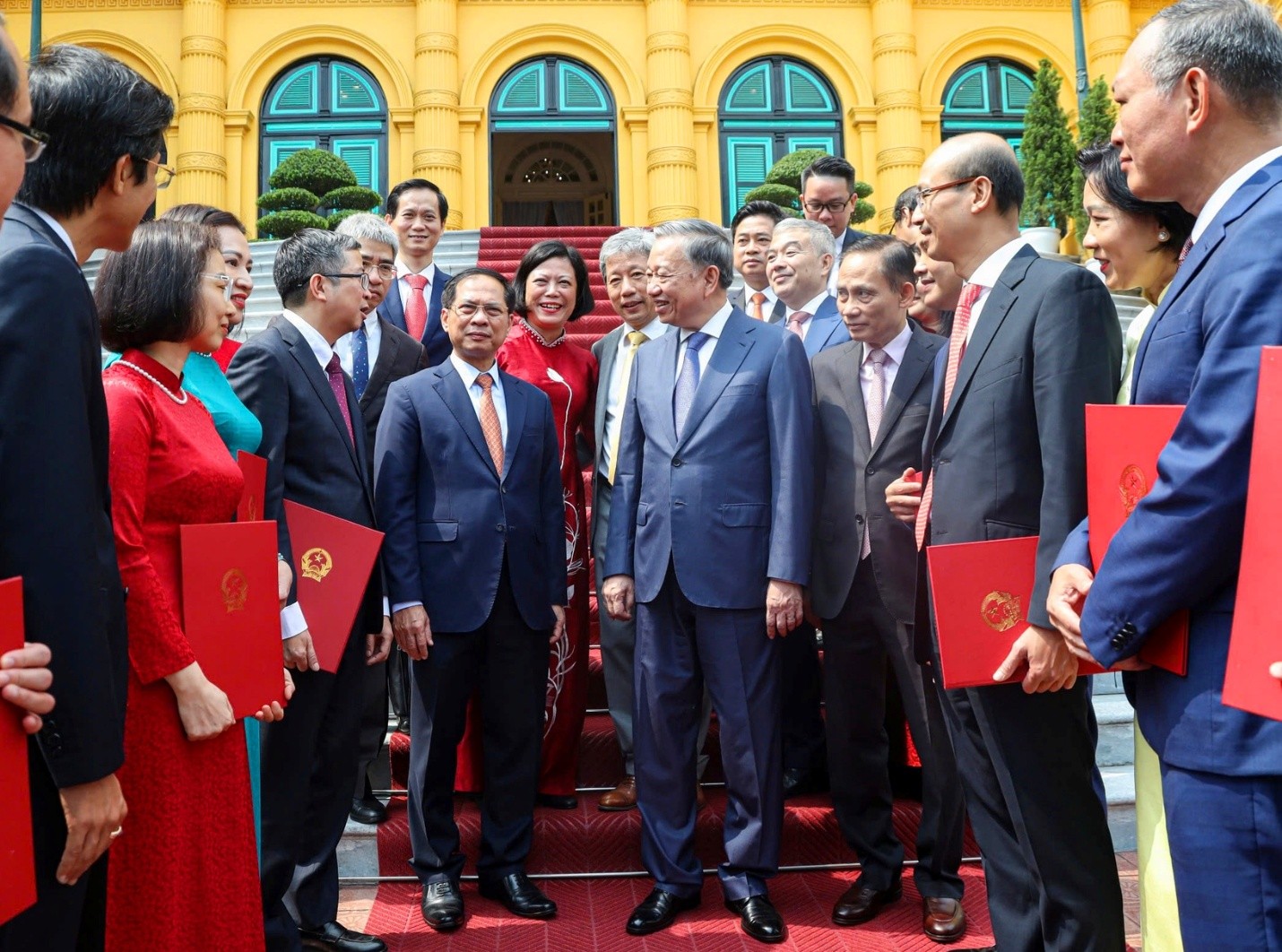
2024年10月14日,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与与获得任命的越南新任驻外大使合影 _图源:baoquocte.vn
80年来,越南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了“民族力量与时代力量相结合”这一理念,始终将越南革命与时代进步潮流和人类共同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进入革新时期,党明确,要实现和平与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合作,而融入国际社会正是国际合作高度发展的一种形式和水平。换言之,融入国际社会就是“让国家融入时代主流,与时代共跳动、同呼吸”,通过与世界接轨增强国家实力。党提出了融入国际社会的路线,首先是经济融入,然后是全面融入,旨在疏通和拓展与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关系,动员外部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家的作用和地位,使越南融入世界政治、国际经济和人类文明。
国家正步入面向繁荣昌盛、“民富、国强、民主、公正、文明”的崛起时代,这就要求我们以新姿态、新定位、新思路和新方法来对待国际融入。越共中央政治局2025年1月24日关于“新形势下融入国际社会”的第59-NQ/TW号决议的诞生,标志着国家融入国际社会进程的历史性转折点,将融入国际社会定位为引领国家迈向新时代的重要推动力。其中,融入国际社会实现了从接受到贡献、从深度融入到全面融入、从后发国家到在新领域崛起和领先的国家地位的转变。
越南共产党将融入国际社会视为巩固政治地位、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国家安全、提升国家在世界格局中影响力的重要战略。融入国际社会经历了从最初有限的、有选择的、偏重于意识形态的融入、单纯的经济融入,到了现在的“深度、广泛、全面融入”等几个阶段。越共九大首次提出“融入国际经济”的方针。越共十一大标志着思路从“融入国际经济”向“在所有领域融入国际社会”的转变。越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4月10日关于融入国际社会的第22-NQ/TW号决议是融入国际社会路线的具体化,提出了“主动和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的方针。最近,越共十三大将这一战略方向再次发展、完善为“主动、积极、全面、深度、广泛、高效融入国际社会”。
经过40年的革新,越南融入国际社会进程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成果。越南从一个饱受围困、孤立的国家,如今已与世界194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与34个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全面伙伴关系,包括联合国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和大国;积极参加7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与各国保持着广泛而务实的政治、防务和安全关系。越南从一个贫穷落后、水平低下、饱受围困和禁运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34大经济体之一,经济规模较1986年增长近100倍,人均收入从不足100美元增加到近5000美元。参与多层次国际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协议,特别是17项自贸协定(FTA),使越南与60多个主要经济体联系起来,更深层次地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使越南跻身世界贸易规模最大的二十国、2019年至今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二十个经济体、全球侨汇收入最大的10个国家之一。
然而,全面、严肃、客观地看待落实融入国际社会方针的成果,仍有一些地方与预期不符,没有达到既定目标,没有满足发展要求,特别是还存在许多制约发展的缺陷、短板、障碍和瓶颈。融入国际社会带来诸多机遇,但也带来诸多挑战和负面影响,例如:不公平竞争、增长不可持续、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偏差”、“文化入侵”、内部“自我演变”、“自我转化”、“信心被侵蚀”等风险。
世界正面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等各领域重大转变所催生的具有时代性的深刻变革。从现在到2030年,是塑造和建立新世界秩序的关键时期。这些变化正在创造一个更加多元的国际环境,为国家带来巨大的机遇,也带来诸多挑战。在新旧秩序的转换时期,中小国家往往处于被动地位,难以适应。在这一转型期,如果我们不能与时俱进,识别和抓住机遇,使国家融入未来10年、20年内的时代潮流,那么落后的风险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突出。
当今时代的力量在于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例如和平、合作与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可持续发展趋势,经济合作与一体化趋势;在于国际社会在创建和巩固一个基于国际法的多极、多中心、民主、公正、平等的世界方面达成的共识,尤其在于基于知识和人类潜能开辟无限发展空间的科技革命。
面对这一历史时刻,国家需要做出历史性的决策。第59-NQ/TW号决议传承了所被肯定的价值观,把握了时代力量的潮流,并以高度革命性、突破性、民族性、科学性和时代性的观点“提升”了对融入国际社会的认识。
首先,与国防安全一起,“加大对外交往和融入国际力度”也是一项重要且常态化的任务。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且常态化的精神是利用外部资源和有利条件,实现早期、远程保卫祖国和发展国家的目标;确保国家民族最高利益,充分确保人民的利益。
第二,在认识上,融入国际社会必须是在党的领导和国家的管理下全民乃至整个政治体系的事业。人民和企业是融入国际的中心、主体、动力、主力军,也是融入国际社会成果的受益者。融入国际社会,但要保持民族特性,融入、融合但不融化。
第三,融入国际社会必须以内部力量的决定性作用为基础,在增强内部力量的同时,充分利用外部力量。内部力量是主要资源,是力量的根源,因此必须始终增强内部力量来确保主动性、独立性和自主性;同时,充分利用各种外部资源,整合和补充内部力量。将民族力量与时代力量有机结合起来,打造崛起时代的越南力量。
第四,融入国际社会是一个既合作又斗争的过程,“合作是为了斗争,斗争是为了合作。注重伙伴的一面,限制对象的一面”。同时,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在融入过程中,必须展现国际社会“积极负责的伙伴”精神,随时准备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共同努力做出贡献。
第五,融入国际社会必须“同步、全面、广泛”,各领域必须在总体战略中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突出重点,并制定合适的路线图和步骤。
国家正面临一场以强有力的全面改革促进发展的革命。第18号决议关于政治体系组织机构重组的“创新精神”、第57号决议关于科技创新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的“突破思想”以及第59号决议关于融入国际社会方向的“行动指南”,将构成党所指出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改善民生”的“战略三部曲”。在当前的革命阶段,必须坚定有效地贯彻落实以下方向:
第一,必须深刻领会和践行融入国际社会的新思路、新认识和新举措。据此,主动、积极、同步、全面、深度、广泛、高效融入国际社会是党的重大战略方向,是发展和保卫祖国、实现社会公正进步、保护环境、维护和弘扬民族文化特色的重要推动力,必须从中央到地方、每个组织、每个人和每家企业得到统一认识。必须向全党、全民、全军深入宣传贯彻党和国家关于融入国际社会的方针政策,以及越南融入国际社会的要求、任务、机遇、权利、责任和义务。
第二,以经济融入为中心,其他领域融入必须促进经济融入,其中首要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创新增长模式、推动数字化转型。聚焦优势和潜力产业,优先动员资源用于交通、能源等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例如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系统,核电站、风电、太阳能发电;减排和实现碳中和,以避免浪费、提高效率,尤其是在当前数字化转型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要有效利用国际经济承诺、协议和机制,特别是新一代自贸协定,以加强利益融合,避免依赖少数合作伙伴。完善国内体制,提高履行国际承诺和协议的能力。制定适当的特殊机制和政策,促进吸引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在作为劳动生产率增长新动力的新兴领域和重要领域,例如信息技术、电信、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等。制定适当的政策,鼓励外国投资者向越南企业和员工转让技术、管理和专业技能。鼓励越南企业在国外有效投资和经营,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品牌。
第三,政治、安全和国防融入必须旨在增强国家的实力和地位,早期、远程地保卫祖国,保邦于未危。融入国际社会必须有效推动已建立的伙伴关系网络,以增进政治互信,调动发展资源,在尊重和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解决现有问题,加强合作。加强与合作伙伴的配合,有效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例如东海问题、水资源安全、粮食安全,污染、流行病控制、网络犯罪、跨国犯罪打击等。凭借新的地位和实力,越南能够争取在合适领域发挥核心、引领和协调作用;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维和、搜救活动;推动国防安全合作多样化,发展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现代化和军民两用的国防安全工业。
第四,必须根据第57-NQ/TW号决议的精神将科技创新作为首要的突破口以及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和完善生产关系的动力。因此,科技创新方面的国际融入必须力求使国内科技标准和规范与国际先进标准和惯例接轨。从而迅速提高国家竞争力,拓展国家发展空间,调动和利用国际资源,大力发挥国内资源来发展优先尖端产业、新兴产业和创新领域。
第五,推动文化、社会、旅游、环境、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全面融入。在文化领域,融入必须与保护、弘扬和推广民族文化相结合;发展具有高质量和全球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内容产业、文化产品和品牌。在医疗卫生领域,加强医疗卫生科学研究与应用合作;在公共卫生领域,按照“东西医结合”的理念,建设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专科医疗中心。在教育培训领域,推动国内培训机构的教育质量标准化、创新和提升,使其达到区域和国际标准。在旅游领域,拓展并实现市场多元化,重点关注客源丰富、消费水平高、逗留时间长的潜在市场。在劳动领域,实施高素质人力资源发展机制,提高越南劳动力的终身学习技能、能力和生产力。最重要的是,制定培养“崛起一代”越南人的战略,力争到2045年,那些十八九岁的青年男女在智力和体能方面能与国际友人们相媲美。
第六,克服履行国际承诺和协议的瓶颈,推动完善制度和政策。推动国际法的梳理和吸收,确保全面、同步、高效地履行越南的义务和承诺。各组织、团体要加强对融入国际社会政策、法律和承诺执行情况的监督。各部委和地方要加大对国际承诺和协议履行的督导力度。同时,要分行业、分领域推进融入国际社会战略制度化、具体化,特别是建立健全绿色经济、数字经济、循环经济、能源转型、数字化转型、减排、航天等法律法规。
第七,贯彻落实第18-NQ/TW号决议精神,完善融入国际社会的专门机构,做到精简、强大、现代化和专业化。目标是提高这些机制的运作效率,促进各级各部门、各地方以及每个人和企业之间在融入国际的协调联动迎来转变。以干部工作为“根本”,建设一支专业知识和技能过硬、达到国际水平、能够参与解决国际争端的从事融入工作的干部队伍。提高地方、民众和企业参与融入国际社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最后,当融入成为所有组织、个人、企业和地方的自觉文化,融入国际社会才能取得成功;要发挥民众、企业和地方的中心作用和积极主动、创造性参与,将国际融入与国内融合、区域融合、行业和领域融合、研究与实施之间的联动结合起来,使得融入带来具体成效。
胡志明主席创造性地运用民族力量与时代力量相结合的思想,找到了救国之路,带领越南摆脱奴役,夺回民族的独立和自由。在当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每个国家的发展都不能孤立存在,不能脱离世界和时代、国际格局的影响。因此,越南必须顺应世界潮流,找到实现和平、稳定、繁荣与发展的道路,在新时代为国家建立更高、更稳固的地位。
越南正面临崛起的重大机遇,但挑战也同样严峻。迄今为止,融入国际社会所取得的成就为下一次突破积累了地位和实力。秉承这一精神,第59-NQ/TW号决议标志着党对今后一个时期融入国际社会的思想和方向发生了重要转变,为国家走向独立、自由、幸福、繁荣和长治久安的辉煌目标注入了新的动力。(完)